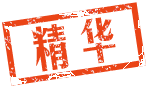|
那村那树那女人 这是一个别说在全国地图上就是在河北省地图上用放大镜都难以找到处在文安洼底的一个小村庄,村东头有一棵老枣树,村里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这棵枣树的年纪。有人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路过文安,站在苏桥的皇恩亭子上往文安洼里一望,什么叫九川雪浪呀,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那浪头都立着,有一人多高。透过浪头尖上,乾隆爷一展他的龙目,看见了一棵枣树,在枣树上象蚂蚁似的趴着一群人,乾隆爷当时就哭了,于是皇恩浩荡,金口大开,给文安人免了好几年的赋税,还给文安人封了个淀神呢。苏桥离俺们那疙瘩少说也有四五十里地,乾隆爷站得再高,能望见四五十里外的一棵枣树,那得嘛眼神呀,鹰眼呀,那时候不可能有现在的望远镜,你别着急,用俺们村的话说就是说得说听得听,小老家前年操死个大老鹰,你爱信不信! 这还不叫悬,庚子年赔款那年,这个村虽然不大,出了不少义和团,义和团大师兄武功那个高呀,这么说吧,八国联军好几百号人,举着条扁担,跟放炮仗似往外放子,那子打在大师兄身上还不如个蚊子呢,别说起包了连个白点都没有。大师兄领着乡亲们就跟八国联军干上了。后来俄国老毛子急了,不知从哪儿推来两带轱辘的大水桶,从水桶里放出来两大碌碡,那个响呀,跟天蹋下来似的。响声过后,人们看到大师兄拄着大刀,从刀上淌着血,背后立着村里的这棵老枣树,连人带树都黑了,但是就是不肯低头,那么直直地戳着。这叫什么?托塔李天王显灵,那些洋鬼子哪见过这阵势,丢枪的丢枪,扔炮的扔炮,夹着尾巴就跑了。 没有人知道这棵老枣树跟了这个村的人相处了多少辈了,也不知道是枣树把这村的人给感染了,还是让这村的人给老枣树感染了,这村的人生活中处处离不开枣树,说话办事跟枣一样,讲究一个嘎崩脆,就连脾气秉性也跟个枣木疙瘩似,用斧子劈半天不甭想劈出半拉缝儿来。别的村的孩子一出生,人家要不给起个金呀玉呀福呀什么的,这村生个男孩子就起个根儿,生个闺女就起个花儿,枣根枣花命硬命贱好养活。 树跟人一样,老了就不跟年轻的似那么刺儿了拉几的,一开春儿小小子就跟疯了似的长在树上,爬树,掏鸟蛋,捅马蜂窝,特别是捅马蜂窝,捅一下就从树上连滚带爬地跑下来,用双手捂着耳朵,嘴里念念有词:“马蜂马蜂别蜇我,我没捅你儿子窝!”这种不打自招此地没银三百两的愚蠢的招式,十个人有一个人十回有一回管用,就成了孩子们捅马蜂窝的护身符,每次捅马蜂窝的时候就跟老和尚念经似的念念有词。 小闺女在枣树底下踢方子、歘子儿、偰包儿、跳皮筋,特别是跳皮筋,一边跳一边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八三五六,三八三五七,三八三九五十一……” 大闺女小伙子在枣树底下搞对象,小伙子打动大姑娘的不是什么海枯石烂之类的词,而是说我会象枣树一样爱你,海枯石烂谁看见过,人们可知道这棵枣树活了人们好几辈了,心眼又实,一个姑娘嫁个枣树一样的男人还不是她天大的福呀。 每年八月十五打枣就跟过大年一样,邻村的也借走亲戚的名凑热闹,年轻的后生们抡圆的膀子,挥舞着竹杆子打枣,孩子们抢着把枣往嘴里塞,老太太们则用衣襟一兜兜地往家里兜,窗台上晒满红了红红的大大的枣。到年根的时候,用石碾子碾出粘面,蒸成年糕,年糕上塞上一些大枣,又香又甜,象大引蜻蜓一样,香味儿把邻村的大姑娘引来,因此这村的小伙子不愁没媳妇。一些枣树叉被人们劈下来做篦叉子腾饽饽,枣木棍子被人们削成擀面杖,枣的香甜味就这样溶进了人们的生活。一些比较歪的枣木棍子被老人削成拐杖,就这样枣树搀扶着人们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这个村的人也跟这棵枣树一样脊梁硬,心眼实成,心肠热。闹年头的时候四乡八县的的乡亲们到文安洼打里地梨儿,村里的人都拉了自己家炕头上,从缸底里崴出自已家的棒子面,贴个饼子,熬点粥,再熬点小鱼儿,小鱼儿,洼里有的是,棒子面虽然不多,但是咱少吃一口也饿不出什么病来,谁要是不是碾子压着手,有个马高蹬短的,大老远的会跑到咱家门口来?! 闹日本的时候,这村里的老娘们小媳妇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都能从这棵枣树底下把自己家当家的送到抗日前线去,男人们开了河的时候撑着船打日本的包船,上了冻的时候撑着拖床闪电般穿梭于日本各据点,给了日本人以沉重的打击。老爷们出门打日本,村里剩下一帮老娘们小媳妇,在枣树底下一边给自己家的负心汉们纳鞋底,一边就数落起大五混来了: “我说这一帮子没良心的,属什么的,一蒙子扎下去就不知道露头了。” 一个老娘们冲大家挤故抗日故眼,就冲着村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小媳妇说开了: “俺们这当家的还好说,一个个都老没垰迟眼了,拉到当街上连狗也不会多看一眼,就不如谁谁的当家的了,人又年轻长得还俊,肯定外面有相好的了,把你甩了吧。” 老太太们一阵轰笑,小媳妇脸也不红心也不跳,一边把锥子在自己的头发里蹭几下,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他就象咱村里这棵老枣树,他的枝爱伸到哪里去,他的根还会跑出咱这个小村?!” 是啊,这村里的老爷们无论是打冬网打风网打地梨儿打日本,无论是面对风口浪尖儿还是面对日本人刺刀,只要心里一想起村里的这棵老枣树心里就暖暖的,只要一望见村里的这棵老枣树的影儿,就疯了似的往家蹿。 有一年村里的老爷们给日本人打急了打疼了,村里出了汉奸,领了一帮子日本人、白脖儿,还牵着大狼狗,把村里的老娘们聚在这棵老枣树底下,逼着老娘们说出八路在哪里?她们不知道八路九路的,就知道自己的当家的把这帮子披着人皮的畜生赶跑了才会有好日子过,你别看平时爱怎么骂自己当家的,哪有娘们傻到把自己家当家的或别人家当家的交给日本人,这天还不蹋下来呀?日本急了,从老娘们当中挑出一个最年轻最俊的,脱光了衣服,用手指粗的钢筋穿透这名妇女的乳房,吊在这个村的老枣树上。平时见个号子都吓个半死的妇女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鲜血吧嗒吧嗒地往下滴,一声不吭。气得汉奸蹦着高地骂大街: “你们,你们真是枣木疙瘩脑袋,八路是你爹呀还是你妈呀,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了,你们看,你们看”,说着故意把手里的绿票子抖得山响,“这是什么,钱,谁要说出八路藏在哪里,看见了吗,这些可就全是你的了,够你们半辈子吃得了,你们到是说话呀!” 没有一人说话。十冬腊月,那名妇女冻了一晚上断气了,日本人不让收尸,赤身裸体愣是在村里挂了十天。 后来解放了,成了队了,这棵枣树上挂了半拉铁华梨,铁华梨一响,人们懒懒地从家里出来,生产队长开始分配活了:“谁谁,赶着马车,到南大疙瘩拉疙瘩去,别忘了,带上两名妇女呀?”妇女们挤故挤故眼,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老队长一拍脑门,胡子一搠:“我说你们的这一帮老太太呀,挣着工分那种又轻尚又美的活轮着你们了,去,拉小菜疙瘩去!少说几字就不行。” 再后来散队了,老枣树退出人们的生活,人们山南海北挣钱去,这棵老枣树再也拴不住年轻后生的心了。只剩下一帮老头老太太拿着小马扎、小蒲团,坐在枣树底,要么晒晒太阳,要么张着没牙的嘴诉说着过去,要么数落着自己家的后生,摇着头:“唉,早晚得遭天谴,这是什么年头呀,哪里有这么糟的,挺大的馒头咬一口,掉了当地,就,唉……”。 爷爷死的时候我们家日子就好过了,我叔混得的开了宝马,无论怎样总要借这个机会在村里风光光。爷爷临咽气的时候叔叔问: “爸,你还要什么,我们一定答应您!” 爷爷眼睛转了一下,抬起手指了指窗外,嘴唇动了动,全家人都把耳朵贴在爷爷的嘴上。大伯哭了: “爹,俺知道您老的心思,您是在咱们村的老枣树底下生的,你还想从老枣底下走。” 爷爷的手放下了,眼睛停止了转动,从眼睛里流下来两颗豆大的眼珠儿。爷爷的灵棚就搭在老宅子前的老枣树底下,灵棚都搭不开,出不车进不去辆的。出爷爷的那天下了一场大雨,整个枣树落下了一地又黄又碎的小花。 再后来村里要盖楼,要把枣树伐了。人们太忙,没有一个人来看这棵枣树一眼,电锯碰到老枣树身上闪着金星儿,老枣树太老了,鲜血早流干了,眼睛早哭开,只有鲜红的骨屑飞溅着,老枣树象一个老人轰然倒下去。九十多岁的奶奶跑过来,又疯又傻,只知道又蹦又跳,拍着巴掌:“好啊,好啊,都走了,走了好啊!” 倒下的岂止是老枣树,是这个村的历史、信仰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