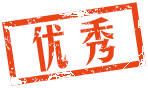|
村边有棵独榴树 在我们村边有一棵独榴树,村里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它的年纪,矮矮的身子,大大的树冠,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树都是碎碎的白色的小花,之后结满一嘟噜一嘟噜小果,其大小比花椒大点,这是上天送给爬洼的人们的最大的礼物,摘一粒放进嘴里,酸酸的涩涩的,一个个呲牙咧嘴,但不一会儿就会延津止渴。 这棵独榴树成了我们童年的天堂,爬树、摔大跤、搂柴火、撞拐,一个字就是疯。在那个物质极度溃乏的年代,孩子们发育得都比较晚,性意识觉醒得更晚,象我九岁才上小学,十四岁才上初中,上小学的时候个子就已经长得差不多了,嘴上长满了密密的绒毛,说话也已变声,小闺儿也是,小花褂子紧紧裹着渐渐发育的身子,但什么也不懂。有时候到洼里打猪菜搂柴火,小闺女撒尿,小小子也会好奇,偷偷地瞟上两眼,这时小闺女就会连笑带骂道:“看什么看,再看就会发眼的!” 我们邻居有个小姑娘,小时候长得什么样记不清了,只知道她是一个跟屁虫,拖着长长的鼻涕,拽着我的手:“哥。”要说有什么不清白吗,就是我常常从家里偷两个菜团子给她吃,她则从家里偷出来饼子夹红糖,那可是当时贵族当中的贵族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品,要知道我们大多数都是吃饼子夹盐粒,有时连香油都不滴,就是滴最多也是两滴,滴多了妈妈从队里回来要挨妈妈打的,一般一瓶香油最少也要吃上半年,你全吃了饼子夹盐粒,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不挨打会非吗? 我劈手一把从她手里夺过来饼子夹红糖: “哥尝尝。” 头也不抬,狼吞虎咽地吃着。她歪着头,笑嬉嬉地望着我,直到我吃到最后一口: “哥,什么味儿呀,好吃吗?” 我一把把饼子塞到她手里,擦擦嘴: “什么行子,太甜了。” 然后撇下她,一个人疯跑去了。她在我后面用拖长的声音、带着哭腔喊道: “哥,等我会儿。” 我们一起打猪菜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筐里的菜抓一把放进她的筐头里,帮她背起来,然后自己再背。小小子们在一起除了打猪菜,就是摔打跤,大人们叫滚屎酱,两只手分别搭在对方的肩上,头顶着头,较劲儿,一会你把他摔倒了,一会他把你摔倒了,在地上打滚,直到把对方骑在身上不能动弹为取胜。我们小子们通过摔大跤个个炼得一身好武艺,那就是铁布衫。那时候条件比较差,一身棉袄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了,我在家排行老四,到了我身上是个什么样子了,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再加上我经常流鼻涕,一会用袖子擦一下,时间长了,那真是浑身铁青,锃光瓦亮。我有少林功夫铁布衫在身,再加上我小时候发育得比较早,个子在同龄人中比较大,自然是摔遍天下无对手。这时候一个小小子起哄: “谁说你摔遍天下无对手,咱们还有一个小闺女,你把她摔倒了我们才服你!” 妹妹尽量缩着身子往后退,哀求道: “哥,我不会摔大跤。” 我不由分说,一把抓过来,自然是没有一个回合,就把她骑在身子底下了,还没等我享受到胜利的喜悦,我妹妹出招了,使出了她看家的独门绝技“九阴白骨爪”,其出手之快之准确大大超乎我的想象,没几下我的脸早跟擦楞子擦得一样了,我大叫一声滚鞍落马,败下阵来。 我妈领着我找到她家,孩子们打了架,大人们反到更亲热了,老姐俩坐在炕头上,有起有落,说得好不热闹: “有你家丫头这样的吗,把人家脸挠成这样,长大了怎么娶个媳妇。我可跟你家说好了,要是娶不上媳妇,你们家可得给俺家当媳妇!” “咱就这么说定了,谁也不许反悔的,走”, 大婶一边说着一边穿鞋下炕: “咱包饺子去!” “不介了,大妹子,俺得赶快家去,家里还有事呢。” 想不到大人们的一句戏谈竟然成了孩子们的口头禅了,跟屁虫再也不跟了,每次她从对面走过来,小伙伴们就拍着巴掌喊道: “小四儿的媳妇来了,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 一边喊着一边夸张地用手指刮着脸。这真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要是看着眼红找你妈要去。我那妹妹捂着脸跑开了,小辫子一甩一甩的。但是没人的时候小声地说: “哥,你把褂子脱下来吧。” 然后从兜里掏出来针线包,粗针大线,索得一个疙瘩一个蛋的。冬天的时候,端着小盆到洋井旁边洗衣服。冬天的洋井水很热,冒着热汽。她用小搓板一下下地搓,不是用冻得红萝卜般的小手捋一捋秀发,脸上冒着热汽,红扑扑的跟个大苹果一样,真好看。我蹲在旁边,用手托着腮,一看就是半天,就是看不够。她用手一撩水: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走,搭衣服去!” “唉。” 这一次我成了跟屁虫了。 她家里条件下不好,很早就拉下来不上了。我去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她到村边的那棵老独榴树下送我,没有接吻,没有拥抱,甚至连手也没有拉过,她塞到我手一把钱,甩下一句话:“别苦了自己,别忘了我!”红红的丝巾,红红的衣服,整个人就象一团红红的火烧云,飘走了,从此我只能仰望。 就在我高考的那年,她嫁人了。出门子那天晚上,她哭得两眼跟桃子似的: “爸,我谁也不嫁,我是四哥的人!” “呸!人家老四早晚会考上大学,早晚会成为公家的人,你也不撒尿照照自己,你配吗!?” 后来听说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电工,人长得很帅,小日子过得很殷实,而我算什么,只不过一穷酸书生,臭老九而已,这样想了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回到家的时候,我一个靠在村边的那棵老独榴树上,顺手摘下一颗独榴,嚼着那段又酸又苦又涩的童年。 |